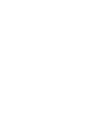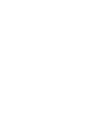庆余年 - 第三百三十六章 京华江南 新风馆的包子 皇子以及
第376章 京华江南新风馆的包子 皇子以及堂上的状师(召唤月票啊……)
“我总觉得我的生命当中缺少了某些东西。”
江南三月最后的一天,春雨润地无声,落於华园亭上,轻柔地像情人互视的柔波。亭下一对男女躺在两把极舒服的椅子上说著话。
海棠看了范閒一眼,摇摇头说道:“你这一世, 可称圆满,又有什么缺憾?”
范閒细思这一世的过往,倒確实称的上是意气风发,肆意妄为,要钱有钱,要权有权, 要人有人,旁人能有的享受自己都有, 旁人做不到的享受自己还是能有,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老大的不满足,人的一生应当怎样渡过,他自忖是清楚的,但真这么过起来,心中那个不知名的渴望却越来越重了。
无关理想人文那些虚无縹渺的东西,他苦著脸说道:“以前有位皇帝,当他老糊涂的时候回思过往,说自己有十大武功, 可称十全老人……当然,这皇帝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糊涂鬼, 人可是位皇帝,比我可要囂张多了,但我却不想当糊涂鬼,也不认为世上真有十全之事。”
“你想当皇帝吗?”海棠似笑非笑著, 就问出了跟在范閒身边的所有人,哪怕是王启年这种心腹之中的心腹都不敢问出来的话题。
海棠觉得范閒真是个妙人,听见自己一个北齐人问出这样大逆不道的问题来,竟是连一丝遮掩也没有,反而很直接地陷入了沉思之中,这个做派若让外人瞧见了,一定认为范閒已经生出了不臣之心。
“当皇帝太累。”范閒头痛说道:“你家的皇帝,我家的皇帝,好像过的虽然舒服,但耗神耗力,实在没什么意思。”
海棠微微一笑,戮破道:“我看你当这个钦差,比当皇帝也轻鬆不到哪里去。”
范閒苦笑说道:“当皇帝要见万人死於面前而不心颤,这一点,我还真做不到。”
海棠微异道:“你不是一向在我面前自忖心思狠厉?”
“杀十几人,杀一百人,我能下得了手。”范閒认真说道:“真要在血海里游泳,我不知道到时候自己有没有这个狠气。”
“所谓量变引起质变,我以前和你说过的。”
他挥挥手,不想再继续这个无趣的话题,躺在椅子上细心听著那些细微不可闻的春雨润泽大地的声音。
亭下渐入安静之中。
……
……
不一时,一位监察院官员穿著莲衣,沉默地出现在了华园的后园入口处,雨水打湿了他的官服,让他浑身上下渗著一股阴寒味道,正是刚从京都来的邓子越。
海棠笑了笑,说道:“看样子,你又要继续忙,继续计划少杀一些人了。”说完这句话,姑娘家也不等范閒回话,很自然地將两只手揣入大兜之中,拖著步子,摇著腰肢,运起村姑步离开了小亭。
范閒微笑看著海棠离开的背影,只见微雨淒迷中,她轻摇而去,雨丝打湿了她鬢角的发,看来这姑娘並没有运起天一道的真气,所谓亲近自然,自然如此,只是那双踩著布鞋的脚,却没有被地上的积水沾污,看来还是做了些手脚。
邓子越见海棠离开,这才沉默地进到亭內,开口说道:“和昨天一样,今天堂上还是在纠缠那些庆律条文,虽然宋世仁牙尖嘴利,在场面上没有落什么下风,但是实质上没有什么进展,只要苏州府抱住庆律不放,夏棲飞有遗嘱在手,也不可能打贏这场官司。”
范閒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隨后便陷入了沉思之中。
今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轰动江南的明家家產一案已经进行到第四日。在经歷了第一天的疾风暴雨之后,后几日的审案陷入了僵局,虽然这是范閒的意料中事,但天天要听下属官员们的回报,范閒也有些不耐烦。
开堂第一日,宋世仁便极为巧妙地用那封遗书,確定了夏棲飞乃明家后人,这个消息马上从苏州府传遍了江南上下,如今所有的人都知道,明家七少爷又活了过来,而且正在和明家长房爭家產。
只是……庆律依经文精神而立,嫡长子的天然继承权早已深植人心,也明写於律条之上,那封遗书似乎已经发挥完了它的歷史作用,对於夏棲飞的愿望,再难起到很大的帮助。
如果夏棲飞想夺回明家庞大的家產,都等若是要推翻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遵循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实在是强大的不是一个人就能推翻的,不仅范閒不行,只怕连庆国皇帝都心有忌惮,如果以这个案例破除了嫡长子的天然继承权,影响太大……
范閒皱起了眉头,忽然想到了一椿很诡异的事情,如果明家的家產官司影响继续扩展,以至於引出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辩论,那宫中那位太子殿下的天然地位?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计划是言冰云擬定,同时经过了陈萍萍的首肯,那位老谋深算的老跛子,不会想不到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莫非……老跛子得了皇帝的暗中指示,这就开始动摇太子天然继承的舆论氛围?
江南明家的事情很大,但如果影响到京都,那事情就愈发的大,以至於范閒根本不想看到这种局面。虽然因为母亲的关係,范閒不可能眼睁睁看著太子继位,一心要杀自己的皇后变成皇太后,但在当前的局面下,直接撩动太子,有可能促使太子捐弃前嫌与长公主二皇子联成一体——如此的结果,范閒暂时不想看到。
范閒陷入了沉默之中,他本来给宋世仁的交代就是,儘量將这官司拖下去,將这个案情打的轰轰烈烈,影响越大越好,如今才发现,这件事情的背后隱藏著那位老跛子的某些想法。
他是信任陈萍萍的,但是……陈萍萍似乎一直基於某种要保护他的理由,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对他点明。而范閒,是一个很愿意学著去了解局势、掌控局势的人。
“看来,等明家事情暂时消停后,我真的要去一趟梧州。”他嘆息著,越发觉得父亲安排自己去梧州见岳父,这是何等样聪慧的判断,看来父亲早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对朝中局势產生某种疑虑,而如今远离京都,真正地面对面帮自己解决问题的,也就只有那位相爷了。
邓子越猜不到范閒真正的忧虑,但也能看出,提司大人对於明家家產的官司有了些不一样的想法,皱眉请示道:“是不是让宋世仁把官司结了?反正夏棲飞如今被確认了明家七子的身份,过些日子,由监察院出面,让他祭祖归宗,依庆律,明家总要给他一些份额,虽然那些份额不怎么起眼,但也达到了大人先前的目標,让他成功地进入明家內部。”
范閒听著邓子越的分析,略感安慰,身边能有一个亲信,感觉確实不错,却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反而仔细问道:“让四处安排夏棲飞……噢,现在应该叫明青城,让明青城与明家老四见面,这件事情怎么样了?”
夏棲飞既然要像一根刺般刺入明家的咽喉,当然要与明家內部的某些异己份子勾结起来,范閒对於豪门大族的阴秽勾当了解的不是很细致,但在前一世的时候,香港无线的电视剧可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邓子越回稟道:“已经接上头了,下月初就让夏棲飞与明家老四见面。”
范閒点点头,这才开始说先前那个问题,轻轻咬了咬发痒的內唇,平静说道:“仍然让宋世仁继续打,把这官司一直打下去!造的声势越大越好……就算打不贏,也不能输!给苏州府压力,不让他们强行结案,一直要打到全天下的士绅百姓都开始想那个问题!”
邓子越抬起头来,微愕说道:“大人,什么问题?”
范閒这发现自己说漏了嘴,笑了笑,想了会儿后,也不打算瞒面前这位亲信,说道:“要让全天下的人都开始思考,是不是嫡长子,就天生应该继承家產。”
邓子越如今身为启年小组的主事官,对於范閒的一切都了解的十分清楚,听著提司大人这话,稍一琢磨,便品出了其中味道,大惊失色,一抱拳劝阻道:“大人,使不得……若让朝中宫中疑大人……之心,那可不好收场。”
范閒微垂眼帘,说道:“子越,你似乎忘了本官的身份,本官姓范,不要担心太多,至於疑我之心……只怕宫里的贵人们会疑我这个先生当的有些逾了本份而已。”
他已经想开了,反正迟早是要和东宫对上,此时先依著陈萍萍的意思,刺刺对方……反正以他如今的权势地位,只要不是谋反,也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更何况,就算有人会认为他造这种舆论是为了自己的將来,但更多的人,应该会认为范閒是在为三皇子做安排。
“这件事情,不要稟告院长大人。”范閒命令道:“只是小事而已。”
邓子越根本无法掩住自己的惊惧,苦笑想著,夺嫡的宣传攻势正式开始,难道还只是小事?
范閒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而失笑起来:“宋世仁不过是个讼棍,难道却是撬动地球的支点?或许是我將这事情想复杂了,公堂上辩辩庆律,和天下旧规只怕扯不上太大关係。”
邓子越没听明白地球这些字眼儿,但也猜到了大概的意思,苦笑应道:“那个宋世仁遇著陈伯常,真可谓是將遇良材,双方打的是火星四溅,可不仅仅在庆律上绕弯子……如果他们在堂上辩的內容真的传扬开去,只怕还真会让人们多想一想那个问题。”
范閒来了兴趣:“噢?那我得去瞧瞧,你去喊三殿下还有大宝,呆会儿全家去苏州府看热闹。”
邓子越苦笑领命。
—————————————————————————
就在细雨的打扮下,三辆全黑的马车离了华园,慢悠悠地驶往离苏州府府衙最近的那条街上,华园眾人这是用午膳去,此时苏州府也在暂时休息,所以大家並不著急。
虽然是离苏州府府衙最近的食街,但其实隔的依然有些远,坐在新风馆苏州分號的三楼,范閒倚栏而立,隔著层层雨幕看著苏州府的方向,恼火说道:“我又不是千里眼,这怎么看热闹?”
邓子越先前派人来订了楼,此时又在布置关防,听著提司大人斥责,不由苦笑说道:“提司大人,这已经是最近了……虽说是闔家出游看热闹,可是总不好三大辆马车开到苏州府去,惊动了官府,也让百姓瞠目,实在是不成。”
范閒嘆息一声说道:“早知如此,在家里吃杨继美厨子就好,何必冒雨出来。”
正说著,身后有人拉了拉他的衣角,他回头一看,正是憨態可掬的大宝,不由诧异问道:“大宝,怎么了?”
大宝咧嘴一笑,说道:“小閒……这……家也……有接堂包。”
大宝用粗粗的手指头指了指桌子上面,一个独一个的蒸屉里,放著独一个大白麵包子,热闹腾腾,內里鲜香渐溢。
范閒嘆了口气,坐在大宝的身边,一边用筷子將烫包分开,又取了个调羹將包子里的油汤勺到大宝的碗里,笑著说道:“这也是新风馆,只不过是在苏州的分號。”
一直小意侍候在一旁的新风馆掌柜赶紧殷勤说道:“是啊,林少爷,虽然江南隔的远,但味道和京都没什么差別,您试试。”
大宝口齿不清地咕噥几句,便对著面前的包子开始发动进攻,將这位掌柜凉在了一边。
倒是范閒有些好奇,问道:“掌柜的,你怎么叫得出来林少爷这三个字?”
掌柜的乾笑两声,討好说道:“提司大人这是哪里话?在京都老號,您老常带著林少爷去新风馆吃饭,这是小店好大的面子,老掌柜每每提及此事,都是骄傲无比,感佩莫名,小的虽然常在苏州,但也知道您与我们新风馆的渊源,小的哪里敢不用心侍候?”
范閒在京都亲掌一处,离一处衙门最近的便是新风馆,所以时常带著大宝去吃他家的接堂包子。其时世风,但凡权贵人物吃饭,不拘何时都要大摆排场,大开宴席,像范閒这种地位的人,对於接堂包子和炸酱麵如此感兴趣的人物还真是不多。所以新风馆虽然味道极美,但因为家常之风,就算在庆国开了三家分號,名气也大,但生意一直普通。
直到后来因为时常接待范閒与林大宝,新风馆在京都才渐渐提升了档次,不知道引来了多少学生士子,要坐一坐诗仙曾坐过的位置,要品一品小范大人念念不忘的包子,让新风馆的老掌柜是喜不自禁。
这位苏州分號的掌柜自然知道范閒是己等的贵客,当然马屁如潮,而且格外用心地铺上些去了腥味的调料,拍的范閒极为舒服,一时间,竟是连看不到苏州府那场戏的鬱闷也消了大半。
……
……
范閒在吃麵条,大宝在啃包子,三殿下却是以极不符合他年龄的稳重,极其斯文有礼地吃著一碗汤圆,思思领著几个小丫环喝了两碗粥,便站到了檐下,看著自天而降的雨水,伸水出檐外接著,嘻笑欢愉,好不热闹。
范閒向来不怎么管下人,所以这些丫头们都很活泼,听著身后传来的欢笑之声,他的心情也好了起来,挥手召来邓子越,说道:“苏州府应该已经开始了,你派人去听听,最好抄点来看看。”
邓子越点点头,去安排人手。
范閒又挥手让高达几名虎卫去旁边吃饭,这才回头继续那碗麵条的工作,其中自然不能免俗地再次在大宝的碟子里抢了块肉馅来吃了,大宝依然如往常那般不吵不闹,大大的个子表示著小小的幽怨。
海棠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时候的新风馆里,都是范閒的下属、下人、与亲人,他很轻鬆快活地赏著雨,挑著白生生的麵条,將心中思虑全数拋开。
发现大宝吃完了,范閒温言问道还要不要,大宝摇了摇头,范閒便从怀里取出手绢,很细心地替大宝將嘴边的油水擦掉。
三皇子看著这一幕,微感诧异,眼中闪过一道古怪的神色。
旁边一桌的虎卫们也愣了愣。
范閒对大宝的爱护细心,世人皆知,但真看到这种场景,依然有很多人无法將这个范閒与那个阴狠厉刻的监察院权臣联繫起来。往常在新风馆吃饭的时候,这一幕就曾经感动过邓子越,触动过沐铁,今日那些虎卫与三殿下对於范閒,或许也会有些新的看法。
对於一个痴呆的大舅哥如此用心,绝对不是简单地可以用“爱屋及乌”来解释,虽然范閒確实极喜爱敬重自己的妻子——这些细节处的表现,如果一直都是范閒用来偽装,用来收买人心的举动,也没有人会相信,常年这样发自真心地做,那人如果不是大奸大恶,就是大圣大贤。
而范閒是哪一种?
……
……
在江南水乡多雨之季,从来不可能產生春雨贵如油这种说法,所以细雨迷濛渐大,老天爷毫不吝惜地滋润灌溉著大地。
范閒眯眼看著檐外的雨水,心思却已经转到了別的地方,院报里说的清楚,今年大江上游的降水並不是很充沛,虽然对於那些灾区的復耕会產生一些影响,但至少暂时不用担心春汛这头可怕的怪物。如此一来,修葺河工的事情,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这时候杨万里应该刚刚入京都报导,大概还需要些时间才能到河运总督衙门。
至於河工所需要的银子……此次內库招標比往年多了八成,明面上的数目已经封库,並且经由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开始运往京都,先入內库,再由皇帝明旨拔出若干入国库,再发往河运总督衙门。
而在暗中,在监察院户部的通力合作下,在范閒父亲所派来的老官们的精心做帐后,已经有一大笔银子,开始经由不同地途径,直接发往了河运所需之处,所用的名目也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一大笔银子里,有一部分是从內库標银,转运司存银里辛苦挤出来的份额,还有一大部分是范閒通过海棠,向北齐小皇帝暂借的银子。
反正那些银子都放在太平钱庄里,范閒先拿来用用,至于归还……那还要等夏棲飞与北边的范思辙打通环节之后,用內库走私的货物慢慢来还。
……
……
这些事情,范閒虽然做足了遮掩的功夫,而且事关北齐皇帝的事情更是掩的结结实实,绝对不会让庆国京都朝廷听到任何风声,但是运银往河运的事情,范閒却早已经在给皇帝的密奏之中提过,这件事情,范閒並无私心,一两银子都没有捞,而且整件事情都是隱秘运行,范閒根本不可能从此事中邀取几丝爱民之名……所有造就的好处,全部归庆国百姓得了,归根结底,也是让那位皇帝老子得了好处,皇帝自然默允了此事。
如今范閒唯一需要向那位皇帝老子解释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笔银子,他究竟是怎么搞到手的。
既然不能说出北齐皇帝这个大金主,就需要一个极好的理由,范閒早在谋划之初,对於这件事情就已经做好了安排,一部分归於这两年的官场经营所得贿银,一部分归於年前顛覆崔家所得的好处,一部分归於下江南之后,在內库转运司里所刮的地皮。
日后如果与皇帝对帐仍然对不上的话,范閒还有最后的一招,就说这银子是五竹叔留给自己的。
谅皇帝也不可能去找五竹对质,如果河运真的大好,说不定龙顏一悦,那皇帝还会用今年如此丰厚的內库標银还范閒一部分。
关於明家,范閒自然也有后手的安排,查处的工作正在慢慢进行,只是目前都被那场光彩夺目的官司遮掩住了。而且对范閒来说,对付明家,確实是一件长期的工作,自己只能逐步蚕食,如果手段真的太猛,將明家欺压的太厉害,影响到了江南的稳定,只怕江南总督薛清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
对於王朝的统治来说,稳定,向来是压倒一切的要求。
明家的存亡,其实並不在江南的官司之上,而在於京都宫中的爭斗上,如果明家的主子——长公主与皇子们倒在了权利的爭斗中,明家自然难保自己的一篮子鸡蛋,如果是范閒输了,明家自然会重新扬眉吐气,夏棲飞又会若丧家之犬四处逃难。
如果范閒与长公主之间依然维持目前不上不下的状態,那么明家就只会像如今这样,被范閒压的苟延残喘,却永远不会轰然倒塌,倔犟而卑屈地活著,挣扎著,等待著。
“大人。”
一声轻喊,將范閒从沉思之中拉了出来,他有些昏沉地摇摇头,这才发现外面的天光比先前黯淡了许多,不仅是雨大了的缘故,也是天时不早了的缘故,他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这一番思考,竟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想到此节,他不由嘆息一声,看来海棠说的对,自己这日子过的,比皇帝也轻鬆不到哪里去。
看了一眼已经玩累了,正伏在栏边小憩的思思,范閒用眼神示意一个小丫头去给她披了件衣服,又看了一眼正和三皇子扭捏不安说著什么的大宝,这才振起精神,拿出看戏的癮头,对邓子越说道:“那边怎么样?”
邓子越笑了笑,將手中的纸递了过去,凑到他耳边说道:“这是记下来的当堂辩词……大人,您看要不要八处將这些辩词结成集子,刊行天下?”
这是一个很毒辣大胆的主意,看来邓子越终於认可了范閒的想法,知道监察院在夺嫡之事中,再也无法像以前那些年般,保持著中立。
范閒笑骂道:“只是流言倒也罢了,这要印成书,宫中岂不是要恨死我?”
听到宫中两字,另一桌上的三皇子往这边望了一眼。范閒装作没有看到,嘆息道:“说到八处……在江南的人手太少,那件事情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效果。”
这说的是在江南宣扬夏棲飞故事的行动,范閒本以为有八处著手,在京都的流言战中都可以打得二皇子毫无还嘴之力,如今有夏棲飞丧母被逐的悽惨故事做剧本,有苏州府的判词作证据,本可以在江南一地闹出声势,將明家这些年营造的善人形象全部毁掉。没有料到明家的实力在江南果然深厚,八处在江南的人太少,明家也派了很多位说书先生在外嚷著,反正就是將这场家產官司与夏棲飞的黑道背景、京都大人的阴谋联繫起来。
两相比较,竟是范閒的名声差了许多,江南百姓虽然相信了夏棲飞是明家的七子,却都认为夏棲飞之所以今年忽然跳出来,就是因为以范閒为代表的京都官员……想欺压江南本地的良民。
范閒想到这事,便是一阵好笑,看来那位一直装病在床的明家主人明青达,果然对於自己的行事风格了解的十分详尽,应对的手段与速度也是无比准確和快速,明青达,果然不简单。
大势在握,不在江南,所以范閒可以满心轻鬆地把与明家的爭执看做一场游戏,对於明青达没有太多的敌意,反而是淡淡欣赏,等他將邓子越呈上来的纸看了一遍之后,更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江南多妙人,京都来的宋世仁可也不差,这苏州府里的官司,竟然已经渐渐脱离了庆律的范畴,开始像陈萍萍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双方引经论典,言必称前魏,拱手必道庄大家,哪里像是在打官司,为了嫡长子继承权这个深入人心的概念,双方竟像是在开一场展前的经筵!
范閒笑著摇摇头,眼前似乎浮现出苏州府上那个紧张之中又带著几丝荒唐的审案场面。
————————————————————————
苏州府的公堂之上,辩论会还在开,这已经是第四天了,双方的主力战將在连番用脑之下,都有些疲惫,於是开堂的间隙也比第一日要拉长了许多,说不了多少,便会有人抢先要求休息下。
苏州知州也明白,夏棲飞那边是想拖,但他没办法,早得了钦差大人关注的口諭,要自己奉公断案,断不能胡乱结案……既然不能胡乱结,当然要由得堂下双方辩。
可是……一个宋世仁,一个陈伯常,都是出名能说的角色,任由他们辩著,只怕可以说上一整年!
苏州知州也看白了,看淡了,所以每逢双方要求休息的时候,都会含笑允许,还吩咐衙役端来凳子给双方坐,至於茶水之类的事情,更不会少。
明兰石面色铁青地坐在凳子上,这些天这位明家少爷也是被拖惨了,家里的生意根本帮不上忙,那几位叔叔纯粹都是些吃乾饭不做事的废物,偏生內库开標之后,往闽北进货的事情都需要族中重要人物,於是只好由一直称病在床的父亲重新站起来,主持这些事情。
明家清楚,钦差大人是想用这官司乱了自己家族的阵脚,从而让自己家在內库那个商场上有些分身无术。只是明家並没有什么太好的应对法子,只好陪著对方一直拖……反正看这局面,官司或许还要拖个一年都说不定,反正不会输就好。
这时候轮到了明家方面发言,那位江南著名讼师陈伯常面色有些灰白,看来这些天废神废力不少,他从身边的学生手中取过滚烫的热毛巾使劲擦了擦脸,重新振作精神,走到堂间,正色说道:
“古之圣人有言所谓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別,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大人,既然夏先生被认定为明家七少爷,但父子之亲,与明家长房並无两端……”
话还没有说完,那边厢的宋世仁已经阴阳怪气截道:“不是夏先生,是明先生,你不要再说错,不然等案子完后,明青城明七老爷可以继续告你。”
宋世仁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双眼有些深陷,他此次单身来江南,一应书僮与学生都来不及带,虽然有监察院的书吏帮忙,但在故纸堆里寻证据,寻有利於己方的经文,总是不易,而对方是本地讼师,身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帮忙,所以连战四日,便是这天下第一讼师,精神也有些挺不住了。
听著宋世仁的话,陈伯常也不著急,笑吟吟地向夏棲飞行礼告歉,又继续说道:“但长幼有序这四字,却不得不慎,明青达明老爷子既然是长房嫡子,当然理所当然有明家家產的处置权。”
他继续高声说道:“礼记丧服四制有云,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
陈伯常越来说来劲,声音也越发的激昂:“自古如是,岂能稍变?庆律早定,夏……明先生何必再纠缠於此?还请大人早早定案才是。”
宋世仁有些困难地站起身来,在夏棲飞关怀的眼神中笑了笑,走到堂前傲然说道:“所谓家產,不过袭位析產二字,陈先生先前所言,本人並无异义,但袭位乃一椿,析產乃另一棒,明老太爷当年亦有爵位,如今也已被明青达承袭,明青城先生对此並不置疑,然袭位只论大小嫡庶,析產却另有说法。”
陈伯常微怒说道:“袭位乃析產之保,位即清晰,析產之权自然呼之欲出。”
袭位与析產,乃是继承之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宋世仁冷笑说道:“可析產乃袭位之基,你先前说庆律,我也来说庆律!”
他一拍手中金扇,高声说道:“庆律辑注第三十四小条明规:家政统於尊长,家財则系公物!我之事主,对家政並无任何意见,但这家財,实系公物,当然要细细析之,至於如何析法,既有明老太爷遗嘱在此,当然要依前尊者!”
陈伯常气不打一处来,哪有这般生硬將袭位与析產分开来论的道理?
“庆律又云: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財不均平者,其罪按卑幼私自动用家財论,第二十贯杖二十!”宋世仁冷冷看著明兰石,一字一句说道:“我之事主自幼被逐出家,这算不算刻意不均?若二十贯杖二十……明家何止二十万贯?我看明家究竟有多少个屁股能够被打!”
明兰石大怒站起。
宋世仁却又转了方向,对著堂上的知州微笑一礼,再道:“此乃庆会典,刑部,卑幼私擅用財条疏中所记,大人当年也是律科出身,应知下民所言不非。”
不等明家再应,宋世仁再傲然说道:“论起律条,我还有一椿,庆律疏义户婚中明言定,即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这是什么罪名?这是盗贼重罪。”
陈伯常双眼一眯,对这位来自京都的讼师好生佩服,明明一个简单无比的家產官司,硬是被他生生割成了袭位与析產两个方面,然后在这个夹缝里像个猴子一样地跳来跳去,步步进逼,虽然自己拿著庆律经文牢牢地站住了立场,但实在想不到,对方竟然连许多年前的那些律法小条文都记的如此清楚。
刚才宋世仁说的那几条庆律,都是朝廷修订律法时忘了改过来的东西,只怕早已消失在书阁的某些老鼠都不屑翻拣的阴暗处,此时却被对方如此细心地找到,而且在公堂之上堂而皇之的用了出来——这讼棍果然厉害!
宋世仁面色寧静,双眼里却是血丝渐现,能將官司打到如今的程度,已经是他的能力极限,袭位析產,真要绕起来確实复杂,他的心中渐渐生出些许把握,就算那封遗嘱最后仍然无效,但至少自己可以尝试著打出个“诸子均分”的效果。
明家的七分之一,可不是小数目。
虽然他不能了解范閒的野望,但钦差大人既然如此看重他,他自然要把这官司打的漂漂亮亮,为讼师这个行业写上最漂亮光彩的一笔。
能够参与到明家家產这种层级的爭斗之中,对於讼师来说,已经是最高的级別,更大一些的事情,比如……那宫里的继承,一个区区讼师哪里有说话的资格?而且如果不是朝廷分成两方,偶成角力之事,明家的家產官司也根本不可能上堂,更不可能立案,宋世仁也就不可能有参与的机会。
所以虽然他十分疲惫,精神上却有一种病態的亢奋,这种机会太少了,自己一定要把握住。
如果宋世仁知道自己在江南打的这场官司,会刺激到某些人敏感的神经,从而间接地促成某些人的合作,並且让范閒与那些人的矛盾提前出现对峙的状態……就算再给他几个青史留名的刺激,他也只会嚇得赶紧隱姓埋名溜掉。
宋世仁没有在意那个问题:所谓家產,大家都是想爭的,不管是明家的,还是皇帝的。
(中饭还没吃,饿死了,出去吃饭,可能又有错別字……大家见谅,最后依然诚恳地號召大家投月票,非常感谢大家投出的每一票,月票这东西,既然开始拉了,我就会继续拉呀拉,拉呀拉……人证?)(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本章完)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