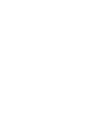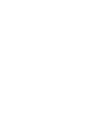庆余年 - 第六百七十章 朝天子 庆庙有雨(要月票……)
第710章 朝天子庆庙有雨(要月票……)
很细微的脚步声在门外的院落里响起,声音极为微弱,尤其是小巷尽头的菜场依旧热闹著,一直將要热闹到暮时,所以这些微弱的脚怕快要被討价还价的隱隱声音所掩盖了。
然而这些微弱的脚步声落在范閒的耳中却是异常清楚, 他微眯著眼凝听著外面的动静,手的中指无名指下意识屈动了两下,却才意识到自己的黑色匕首早已遗落在了皇宫前的秋雨中,此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可是他依然平静,依然有十足的信心將外面的来人一击制伏。
洪亦青紧握著匕首,小心而沉默地蹲守在门背后, 屏住了呼息, 看著越来越近的那个人影, 那个人影很奇怪直接走到了门口,然后轻轻敲了两下,听到那种有节奏的敲门声,洪亦青的神態明显放鬆了下来,因为这种暗號是启年小组內部的身份识別。
范閒却没有放鬆,因为他其实並没有十足的把握,启年小组究竟有没有被朝廷渗入进来,或是已经接触到了外围。毕竟从达州的事情,高达的存在倒推出去, 宫里那位皇帝陛下对於情报方面的重视远远超出了范閒甚至是陈萍萍的判断,而且內廷在监察院內部也一定藏著许多的死忠, 不然言冰云也极难在这七天之內就控制住了那座阴森的院子。
“是我。”门外那个人影似乎知道屋內有人,沙哑著声音说道。
听到这个声音,洪亦青没有听出来人是谁,范閒的脸色却马上变了,有些喜悦, 有些伤感,有些意外。
门被推开了,一个有著一张陌生面孔,穿著京都郊外常见菜农服饰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王头儿?”洪亦青压低了声音,不敢置信地看著来人,从那双眼瞳里熟悉的温厚笑意分辩出了对方的身份,毕竟他是被王启年亲手挑入小组的人,对於王启年还是比较熟悉,只是……在监察院绝大多数官员的心中,王启年三年前就因为大东山叛乱一事而死,怎么今天却又活生生地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乔装打扮后的王启年拍了拍洪亦青的肩膀,然后凝神静气,十分认真地强抑激动站在桌后的范閒深深行了一礼。
“改日再聊吧,总有再见的时候,办正事儿去。”范閒笑了起来,將手中的小刀扔给了洪亦青。洪亦青此时脸上依然是一副神魂未定的模样,却也知道事情急迫,不敢多耽搁,向二人分別行礼,便向著西方的那片草原去了,去寻那个叫做松芝仙令的人物。
……
……
范閒从桌后走了出来,走到王启年的面前,静静地看了他片刻,然后与他抱了抱,用力地拍了拍他的后背,然后站直了身体,很轻易地看出王启年易容之后依然掩饰不住的疲惫。
范閒望著王启年,王启年也望著他,两个个久久没有言语,许久之后,范閒才嘆了口气,说道:“真是许久未见了。”
在东夷城返京的道路上,王启年拼命拦截住监察院的马队,向范閒通知了那个惊天的消息,那时节,两个人根本没有时间说些什么,嘆些什么,范閒便起身直突京都,去救陈萍萍。
仔细算来,范閒归京恰好八日,王启年便再次赶回了京都,而且在那之前,王启年已经有一次从达州直插东北的艰难飞奔之旅,两次长途的跋涉,著实让年纪已经不小的王启年疲惫到了极点,纵使他是监察院双翼之一,此时也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范閒將他扶到椅子上坐下,沉默片刻后说道:“这几年你在哪儿呢?”这句话问的很淡,其实很浓,范閒知道他没有死,也知道在陈萍萍的安排下,逃离大东山的王启年及一家子都隱姓埋名起来,为了老王家的安全,范閒只是略查了查后便放弃了这个工作。在这三年里,范閒时常想起他,想起这个自己最亲密的下属,知道自己最多秘密的可爱的老王头。
“其实没有出过京,一直在院长的身边,一直看著大人您,知道您过的好,就行了。”三年未见,二人並未生出丝毫疏离的感觉,王启年沙著声音说道。
范閒沉默很久后说道:“我……回来的晚了。”
这说的是陈萍萍的事情,王启年低下头,也沉默了很久,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是我报信报的太晚了。”
其实他们两个人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而只是依然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那件事情,一股淡淡的悲伤与自责情绪就这样充溢在房间里。
“家里可好?”
“好,朝廷应该查不到。”
“那就好,回我身边吧。”
“好。”
……
……
这样自然到了极点的对答之后,范閒冰凉了许久的心难得温暖了一丝丝,轻声问道:“让你跟著大队去东夷城,怎么又回来了?”
“黑骑四千五名满员已入东夷城范围,其中一路此时应该开始向十家村,院长交代的事情已毕,所以我就赶了回来。只是耽搁了两天,所以缓了些。”王启年说道:“荆戈,七处那个老头儿,还有宗追都在那一路里,院长留下来的最强大的力量都要集中到十家村。”
范閒沉默片刻,面容复杂地笑道:“想不到十家村的事情也没能瞒过他。”
“院长要知道些什么事情,总是能知道的。”王启年说道。
“不说这些了。”范閒嘆息了一声:“有你在身边,很多事情做起来就方便多了,至少像今天这样,我何至於还要耗七天时间,才能钻出那张网来。”
略敘几句后,王启年便清楚地了解了最近京都发生的事情,他忍不住幽幽嘆息道:“若监察院还在手里,做起事情就方便多了。”
如今范閒真正能够相信能够使动的人,除了启年小组之外,便是遍布天下的那些亲信下属,然而监察院的本部已经开始逐渐分崩离析,尤其是言冰云父子二人世代控制著四处,长此以往,范閒及那批老臣子在院內的影响力只怕会越来越弱。
“这天下毕竟还是陛下的天下,就算一开始的时候,院內官员会心痛院长的遭遇,可是时日久了,他们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忠君爱国嘛……”范閒的唇角微翘,他也只有在极少数人面前,才会表现出来对於皇权的蔑视和不屑一顾,“又有几个人敢正面对抗那把椅子?”
“言大人不是那种人。”王启年沙哑著声音说道,这句话里的言大人自然指的是言若海,“我不明白言冰云是怎么想的。”
“院长对他有交代。”范閒微闭著眼睛说道:“院长不愿意天下因为他而流血,並且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我手中力量的存续,把我与他割裂,如果我……像他想像那样表现的好,用不了几年,我会再爬起来,那时候……陛下或许也老了。”
是的,这便是陈萍萍的愿望,而这种愿望所表现出来的外象,却符合言冰云他很认可的天下为重的態度,所以言冰云很沉稳而执著地按照陈萍萍的布置走了下去。
接下来,是需要看范閒的態度而已。
“言冰云不会眼看著监察院变成我復仇的机器,公器不能么用,这大概是一种很先进的理念。”范閒平静说道:“然而他忘记了,这天下便是陛下的一家天下,所有的官员武力都是陛下的私器。”
他微嘲说道:“可惜我们的小言公子却是看不明白这个,忠臣逆子,不是这么好当的,希望他以后在监察院里能坐的安稳些。”
王启年听出来了,范閒对於言冰云並没有太大的怨恨之意,眼睛微眯说道:“接下来怎么做?”
“你先休息。一万年太久,但也不能只爭朝夕。”范閒站在王启年的身边,轻轻地摁了摁他有些垮下去的肩膀,和声说道:“你这些日子也累了,在京里择个地方呆呆,估摸著也没几个人能找到你,然后……我有事情交给你去办。”
以王启年的追踪匿跡能力,就算朝廷在范府外的大网依旧洒著,只怕也拦不住他与范閒的碰头,有了他,范閒的身体虽然被留在京都,但是说话的声音终於可以传出去,再不像这七日里过的如此艰难。
王启年已经知道了今天范閒通过启年小组往天下各处发出的信息,他並没有对这个计划做出任何的建议,他只是不清楚,范閒究竟是想就此揭牌,而是说只是被动地进行著防御,將那些实力隱藏在京都外,再等待著一个合適的机会爆发出来。
“我希望子越能够活著从西凉出来。”范閒眉头微微忧鬱,“我本打算让他回到北齐去做这件事情,只是一直有些不放心,毕竟他们就算愿意跟隨我,但毕竟那是因为我是庆人,甚至……可能在他们眼中,我本身就是皇室的一份子,所以哪怕面对陛下,他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可若是北齐……”
他抬起头来,看著王启年:“若我要带著你叛国,你会跟著我走吗?”
王启年苦笑著站起身来,说道:“前些年这种事情做的少吗?就算大人要带我去土里,我也只好去。”
范閒笑了,说道:“所以说,这件事情只有你去做,我才放心。”
……
……
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了这座小院,註定的,这间花了一百二十两银子的小院从今以后,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內都不会有人再来,只有孤独的雨滴和寂寞的蛛网会陪伴著那些平滑的纸张、冰凉的墨块。
一顶大大的帽子遮在了范閒的头顶,顺著菜场里泥泞的道路,他远远地缀著王启年那个泯然眾人的身影,直到最后跟丟了他才放心。一方面是確认小院的外面没有埋伏,另一方面则是安定他自己的心,连自己跟王启年都跟丟了,这座京都里又有谁能跟住?
办完了这一切,范閒的心情放轻鬆了一些,就如大前天终於停止了秋雨的天空一般,虽未放晴,还有淡淡的乌云,可是终究可以隨风飘一飘,漏出些清光入人间,不至於一味的沉重与阴寒。
天下事终究要天下毕,抢在皇帝陛下动手之前,范閒要儘可能地保存著自己手头的实力,这样將来一朝摊牌,他才能够拥有足够的实力与武器……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似乎在哪个地方犯了错误,那种隱约间的警惕,就像是一抹云一样总在他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却总也看不清楚形状。
將菜场甩离在身后,將那些热闹的平凡的不忍苛责的市井声音拋在脑后,范閒沿著京都几座城门通往皇宫方向的辐形大街向著南城方向行去,事情已经办完了,启年小组的人手也集体撤出了京都,他不需要再担心什么,便是被软禁在府內,也不是如何难以承受的痛苦。
然而路上要经过皇宫,远远地经过皇宫,范閒止不住的痛苦了起来,他强行让自己不去想几天前的那一幕幕画面,却忍不住开始想妹妹如今在宫里究竟过的怎么样。虽然戴公公说了,陛下待若若如子女一般,但是若若如今的身份毕竟是人质,她自己也心知肚明,想必在宫里的日子有些难熬。
这是皇帝陛下很轻描淡写的一笔,却直接將范閒奋力涂抹的画卷划破了。范閒不可能离开京都,全因为这一点。
下雨了,范閒微微低头,让衣帽遮著那些细微的雨滴,沉默地在皇宫注视下离开,此处森严,街上行人並不多,却也能听见几句咒骂天气的话,想必连绵的秋雨刚歇两日又落了下来,让京都的人们很是不满。
不满也有习惯成麻木的时候,今天的雨並不大,范閒就这样沉默地往府里走著,就像一个被迫投向牢狱的囚徒,实在是没有法子。他一面走一面思考,將皇宫里那位与自己做了最全方面的对比,然后最后他把思绪放到了那些麻衣苦修士的身上。
从陈萍萍归京开始,一直到他入狱,一直到范閒闯法场,那些麻衣笠帽的苦修士便突然地出现在了皇宫里,监察院里,法场上。这些苦修士实力虽然厉害,但並不足以令范閒太过心悸,只是他有些想不明白,而且因为这些苦修士联想到那个虚无縹渺,但范閒知道確实存在的……神庙。
庆国向来对神道保存著敬而远之的態度,並不像北齐那样天一道浸透了官场民生。尤其是强大的皇帝陛下出现之后,庆庙在庆国生活中的地位急转直下,彻底沦为了附属品和花边,那些散布於天下人数並不多的庆庙苦修士,更成为了被人们遗忘的对象。
为什么这些被遗忘的人们却在这个时刻出现在了京都,出现在了皇帝陛下的身边?难道说皇帝陛下已经完全控制了庆庙?可是庆庙大祭祀当年死的蹊蹺,二祭祀三石大师死的窝囊,大东山上庆庙的祭祀们更有一大半是死在了陛下的怒火下,这些庆庙的苦修士为什么会彻底倒向陛下?
难道真如陈萍萍当年所言,自己隱隱猜到……当年的皇帝,真的曾经接触过神庙的意志?而这些苦修士则是因为如此,才会不记多年之仇,站在了陛下的身边,助他在这世间散发光芒?
雨没有变大,天地间自有机缘,当范閒从细细雨丝里摆脱思考,下意识抬头一望时,便看见了身前不远处的庆庙。
那座浑体黝黑,隱有青檐,於荒凉安静街畔,上承天雨,不惹微尘,外方长墙,內有圆塔静立的庆庙。
范閒怔怔地看著这座清秀的建筑,心里不知是何滋味,在这座庙里,他曾经与皇帝擦肩而过,曾经在那方帷下看见了爱啃鸡腿儿的姑娘,也曾经仔细地研究过那些檐下绘著的古怪壁画,然而他真正想搞清楚的事情,却一件也没有搞清楚过。
他本应回府,此时却下意识里抬步拾阶而入,穿过那扇极少关闭的庙门,直接走入了庙中。在细细秋雨的陪伴下,他在庙里缓缓地行走著,这些天来的疲乏与怨恨之意却很奇妙地也减少了许多,不知道是这座庆庙本身便有的神妙气氛,还是这里安静的空间,安静的让人懒得思考。
很自然地走到了后庙处,范閒的身形却忽然滯了一滯,因为他看见后庙那座矮小的建筑门口,一位穿著麻衣,戴著笠帽的苦修士正皱著眉头看著自己。
范閒欲退,然而那名苦修士却在此时开口了,他一开口便满是讚嘆之意,双手合什对著天空里的雨滴嘆息道:“天意自有遭逢,范公子,我们一直想去找您,没有想到,您却来了。”
被人看破了真面目,范閒却也毫不动容,平静地看著那名苦修士轻声说道:“你们?为何找我?”
那名苦修士的右手上提著一个铃当,此时轻轻地敲了一下,清脆的铃声迅即穿透了细细的雨丝,传遍了整座庆庙。正如范閒第一次来庆庙时那样,这座庙宇並没有什么香火,除了各州郡来的游客们,大概没有谁愿意来这里,所以今日的庆庙依旧清静,这声清脆铃响没有引起任何异动,只是引来了……十几名苦修士。
穿著同等式样麻衣,戴著极为相似的古旧笠帽的苦修士们,从庆庙的各个方向走了出来,隱隱地將范閒围在了正中,就在那方圆塔的下面。
范閒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开始缓缓地提运著体內两个周天里未曾停止过的真气脉流,冷漠地看著最先前的那名苦修士平静说道:“这座庙宇一向清静,你们不在天下传道,何必回来扰此地清静?”
“范公子宅心仁厚,深体上天之德,在江南修杭州会,聚天下之財富於河工,我等废人行走各郡,多闻公子仁名,多见公子恩德,一直盼望一见。”
那名苦修士低首行礼,他一直称范閒为范公子,而不是范大人,那是因为如今京都皆知,范閒身上所有的官位,都已经被皇帝陛下剥夺了。
“我不认为你们是专程来讚美我的。”范閒微微低头,眉头微微一皱,他是真没有想到心念一动入庙一看,却遇见了这样一群怪人,难道真像那名苦修士所言,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然而这些古怪的苦修士们却真的像是专程来讚美范閒的,他们取下笠帽,对著正中的范閒恭敬跪了下去,拜了下去,诚意讚美祈福。范閒面色漠然,心头却是大震,细细雨丝和祈福之声交织在一起,场间气氛十分怪异。
苦修士们没有穿鞋的习惯,粗糙的双足在雨水里泡的有些发白,他们齐齐跪在湿漉漉的地上,看上去就像是青蛙一样可笑,然而他们身上所释放出来的强大气息和说出来的话並不可笑。
这股强大的气息是这十几名苦修士实势和谐统一后的气息,其纯其正令人不敢轻视。如念咒一般的诚恳话语在雨中响了起来,伴隨著雨水中发亮的十几个光头,令人生厌。
“我等为天下苍生计,恳求范公子入宫请罪,以慰帝心。”
范閒的脸色微微发白,只是一瞬间,他就知道这些苦修士想做什么。庆帝与范閒这一对君臣父子间的隔阂爭执已经连绵七日,没有一方做过任何后退的表达。
为天下苍生计?那自然是有人必须认错,有人必须退让,庆国只能允许有一个光彩夺目的领袖,而在这些苦修士们看来,这个人自然是伟大的皇帝陛下。
苦修士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庆国眼下最大的危机,不知道出於什么考虑,他们决定替皇帝陛下来劝服范閒,在他们的心中,甚至天下万民的心中,只要范閒重新归於陛下的光彩照耀之下,庆国乃至天下,必將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將来。
“若我不愿?”范閒看著这些没有怎么接触过的僧侣们,轻声说道。
场间一片死一般的沉默,只有细雨还在下著,落在苦修士们的光头上,檐上的雨水在滴嗒著,落在庆庙的青石板上。许久之后,十几道或粗或细,或大或小,却均是坚毅无比,圣洁无比的声音响起。
“为天下苍生,请您安息。”
……
……
(今天写的满足了,明天再写,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上边的朋友……请投月票支持。)
(本章完)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